
本网讯(文/崔书克 邓海祥)近期,《中国中医药报》分别在2018年12月10和12月17日刊登我校崔书克教授和学生邓海祥的三篇文章,充分展示了我校师生在中医文化方面的良好积淀。现将三篇文章刊发如下。


2018年12月17日第8版刊登崔书克《悼念二月河先生》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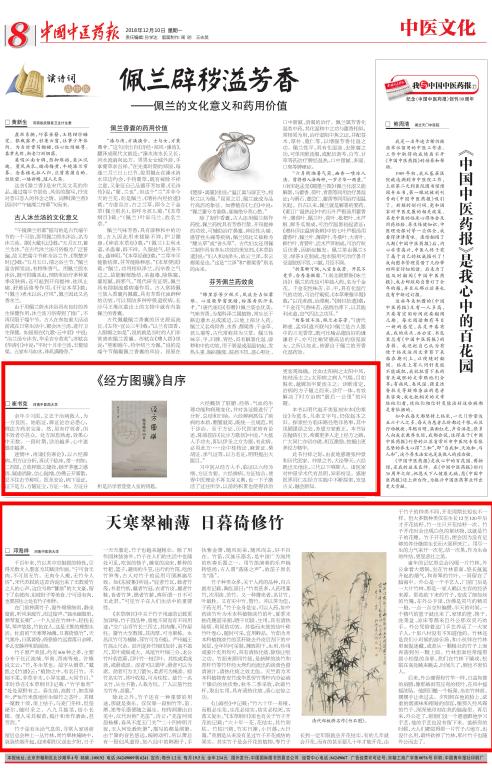
2018年12月10日第8版刊登我校师生两篇文章
《经方图骥》自序
河南中医药大学 崔书克
余年少习医,立志于治病救人,为一方良医。始临证,辨证论治必悉心,理法方药求完备。然,虽有疗效者,但不效者亦甚众。处方深思熟虑,效果心中无数。一段时期,诊治越多,心中迷惑亦越多。
迷惘中,再诵《伤寒论》,以六经辨病,用方证分析,再试于临床,常一剂知,二剂显,立收桴鼓之捷效,顿开茅塞之感悟,疑虑消除,信心陡增,仿佛云开雾散,忍不住击节称叹。医圣宏论,病下是证,证下是方,方随证立,方证一体。方证分析是后学者登堂入室的钥匙。
六经概括了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对各证候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归纳。六经辨病抓住了疾病的本质,删繁就简,既统一且规范,利于诊治。至于方证,历代医家皆有论述,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说,“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习中医从经方入手,临证以六经为纲、方证为要。六经辨病,方证结合,使得中医理论不再文深义奥,也一下子激活了过往所学,以前的积累也使得诊治更客观准确。比如太阳病之太阳中风,桂枝汤主之;太阳病之病人气喘,目如脱状,越婢加半夏汤主之。诊断甫定,治病的方子随之而来,诊疗一体,有效解决了时方治病“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本书以明代赵开美复刻宋本《伤寒论》为蓝本,凡条文字句,仍依赵本之旧。探索经方临床路径绝非易事,其中浅陋谬误之处,务望方家教正。本书旨在抛砖引玉,希冀更多人走上经方之路,广大同仁亦切亦磋,相互激励,挖掘出更多经方精华。
此书付梓之际,由衷地感谢张仲景和历代医家。仲景之书,大论擎天,六经既出无他论,三代以下唯斯人。诸医家对仲景学术代有昌明,异彩纷呈。感谢医界同仁在经方实践中不断探索,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
河南中医药大学 邓海祥
千百年来,竹以其中空挺拔的特性,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其赋诗作画。“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宋代苏轼的这首诗说出来了无数爱竹之人的心声,这位号称“饕翁”的大文豪,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美食,宁可没有肉,也要居住之处有竹子相伴。
在门前种满竹子,窗外绵绵细雨,静坐窗前,听风来疏竹,雨过留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一个人坐在竹林中,轻抚长琴,琴声悠悠,竹色宜人,这是王维的理想生活。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天气寒冷,日落黄昏,倚靠修竹远看落日余晖,多么安静祥和的画面。
竹子原产我国,约有500种之多,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华南、西南等地。许慎说文云:“竹,冬生草也。故字从倒草。”戴凯之《竹谱》云:“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实惠,大同节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竹字象形”“处处原野有之。春生苗,高数寸,细茎绿叶,俨如竹米落地所生细竹之茎叶。其根一窠数十须,须上结子,与麦门冬样,但坚硬尔,随时采之。八九月抽茎,结小长穗。俚人采其根苗,捣汁和米作酒曲,甚芳烈。”
竹子是有生活气息的,寻常人家房前屋后总会种上一丛竹林,青竹翠林掩映中,袅袅炊烟升起,迎来朝阳又送走夕阳,日子一天天溜走,竹子也越来越粗壮。除了用作园林装饰外,竹子在人们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吃饭的筷子,睡觉的凉床,耕种的竹耙、篮子,避雨的斗笠,出行的竹筏,吃的竹笋等,古人对竹子的运用可谓淋漓尽致。如《东坡集》所说:“庇者竹瓦,载者竹筏,书者竹纸,戴者竹冠,衣者竹皮,履者竹鞋,食者竹笋,燃者竹薪,真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可见竹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本草纲目》中关于竹子用途的记载更加详细,竹子因品种、质地不同而有不同用途:“交广由吾竹长三四丈,其肉薄,可作屋柱。簹竹大至数围,其肉厚,可为梁栋。永昌汉竹可为桶斛,荨竹可为舟船。严州越王竹高止尺余。辰州龙孙竹细仅如针,高不盈尺,其叶或细或大。凤尾竹叶细三分,龙公竹叶若芭蕉,百叶竹一枝百叶。其性或柔或劲,或滑或涩。涩者可以错甲,滑者可以为席。劲者可为戈刀箭矢,柔者可为绳索。棕竹名实竹,其叶收棕,可为柱杖。慈竹一名义竹,从生不散,人栽为玩。广人以筋竹丝为竹布,甚脆。”
除此之外,竹子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奏乐。仅仅靠一段细竹竿,笛、萧、笙等乐器便随之诞生。相传洞箫出自羌中,汉代时称“羌笛”,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描写的都是洞箫。由于箫的音色悠远,婉转动听,所以萧总有一股仙风道骨,如八仙中的韩湘子,手执紫金箫,随风而来,随风而去,好不自在。竹笛,汉族乐器名,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之一。用竹笛演奏的乐声婉转悠扬,古人谓“荡涤之声”,故笛子原名为“涤”。
竹子种类众多,关于入药的品种,自古就有记载,陶弘景曰:“竹类甚多,入药用蓳竹,次用淡、苦竹。又一种薄壳者,名甘竹,叶最胜。又有实中竹、篁竹。并以笋为佳,于药无用。”竹子全身是宝,可以入药,如中药淡竹叶为禾本科植物淡竹的叶,夏季末抽花穗前采割,晒干切段,生用,具有清热除烦、利尿的功效。其卷而未放的幼叶称竹叶卷心,随时可采,宜用鲜品。竹茹为禾本科植物淡竹的茎秆除去外皮后刮下的中间层,全年均可采制,摊放阴干,生用、炒用或姜汁炙用均可,具有清热化痰、除烦止呕之功。竹沥来源同竹茹,是新鲜的淡竹和青杆竹等竹杆经火烤灼而流出的淡黄色澄清液汁,清热化痰之效尤佳。天竺黄为禾本科植物青皮竹或华思劳竹等杆内分泌液干燥后的块状物,秋冬二季采收,砍破竹杆,取出生用,具有清热化痰、清心定惊之功。
《山海经》中记载:“竹六十年一易根,而根必生花,生花必结实,结实必枯死,实落又复生。”《本草纲目》里也有关于竹子开花的记载:“六十年一花,花结实,其竹则枯。竹枯曰箹,竹实曰箯,小曰蓧,大曰簜。”我倒是从来没有见过竹子开花或结的果实。其实竹子是会开花的植物,等竹子长到一定年限就会开花结实,有的几年就会开花,而有的甚至要几十年才能开花,由于竹子的种类不同,开花周期长短也不一样。但大多数种类仅在生长12至120年后才开花结籽,竹一生只开花结籽一次。竹子开花时会出现白色的絮状物,这就是竹子的花穗。竹子开花后,便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养分继续生长而大面积死亡。用尽一生的力气来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作为生命的终结,更显悲壮之美。
童年的记忆里总会闪现一片竹林,外公拿着大烟锅,坐在竹林前面,悠长氤氲升起的烟气,和青翠的竹叶,一同留在了脑海中。外公是一个手艺人,门前门后是一大片竹林,那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那些砍下来的竹子,变成了细如丝的竹篾,在外公手里,仿佛是灵巧的精灵一般,一点一点交织编攒,半天的时间,一个精巧的篮子就出来了,家里的筐、筷子、洗菜盆、凉床等都来自外公那双灵巧的手。外公凭借着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他的。竹林还是我们小时候的游乐场,和小伙伴在竹林里面捉迷藏,或者从一颗粗壮的竹子上面再荡到另一颗上面。竹林里面经常能看到小松鼠的身影,我们在竹林下嬉戏,松鼠在高处跳来跳去,时间久了,倒也不害怕人。
后来,外公瘦得和竹竿一样,日益佝偻的肩膀,像那被雨雪压弯的枝叶,在风中摇摇欲坠。他照旧搬一个板凳,坐在竹林前,摆摆手让我过去。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浓重的烟熏味和褶皱的面容,像那久经风霜的竹子,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再后来,外公走了,舅舅们没一个愿意跟他学习手艺,他的手艺也没有留下来。盖新房的时候,大人们都觉得那一片竹子占地方,也没什么用,最终砍掉了竹林,那片竹子也随外公而去了。
悼念二月河先生
河南中医药大学 崔书克
惊悉作家二月河先生于12月15日病逝,着实不敢相信,求证于南阳亲友,方知先生已赴京就治多日,近日病情加剧,经救无效,不幸西去,令人唏嘘。
我和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末。那年夏天我常去南阳梅溪路的一家健身房锻炼身体,而先生拿一柄大蒲扇,就端坐在健身房马路边的树荫下,悠然地摇几下蒲扇,笑看着大街上车马喧嚣。我第一次看到时,立即就想到“大隐者,隐于市”的高士,人虽在繁华都市中,而心灵乃一方净土,不与世争,不与世浊,独善其身,优哉游哉。
有一次儿子随我去健身,老远便喊“凌爷爷——”先生便走上前来,抱着儿子,很是亲切。儿子就问:“凌爷爷,你姓凌,怎么叫二月河呀?”先生顿时哈哈大笑道:“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七九天就是农历二月天了,黄河凌汛解放,万排齐发向东流——喽。”先生说流字时,故意拉得很长,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在夕阳余晖下,脸庞愈发显得浑圆、亮堂,洋溢着自豪和幸福,仿佛大河就在脚下,万排齐发,滚滚东流,澎湃着磅礴大气。
我那时已在卫校任职,又是主治医师,先生常说:“你的职业很令人羡慕,教师塑造人的灵魂,十年树木易,百年树人难;医生常救人于危难之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福报很大啊!”先生说起曾获得过南阳市自学成才奖一事,自然把学问看得甚高。谈及中医药,先生常常赞不绝口,尤其是罹患脑梗死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后,多次感慨道:“纵览中国历史,中医药学是当之无愧的国学精华,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防病治病理念,与西医相比,各有千秋,如能取长补短,有机结合,一定会为人类健康做出大贡献!”我知是先生勉励后学,谨记在心,教学必悉心备课,亦教亦学,不敢懈怠误人,行医时辨证论治必悉心,理法方药求完备。面对病患,常怀敬畏之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知道先生身体不佳,曾去南阳探视,无奈来去匆匆,未及深谈。前几年有亲友从南阳送来先生签字的《二月河文集》,先生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端。皇皇巨作13卷,花费了先生太多心血,长年累月的辛劳,使得肥胖、高血压、哮喘、糖尿病、脑梗死接踵而来。早几年,我受聘为国家中医药局全国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先生曾来电鼓励。随后我把讲稿汇聚成册,出版了《脑卒中防治》一书,为先生健康计,早该送出一本。之所以未能送出,一则想亲手送交,当面请教;二则总认为是一本小册子,科普读物,送给大方之家,实在局促。就这样,犹豫再三,终未送出,竟成永憾。
伏牛垂首,白河呜咽。先生的离去是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重大损失。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大气磅礴,与康熙大帝的玉宇呈祥,与雍正皇帝的雕弓天狼,与乾隆皇帝的日落长河一样,都牢牢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编辑 苗苗;审核 王秋安)